澳門蓮峰古廟 許斌攝
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沒有母親,而我的父親也比同班同學的爸爸老一些。父親很努力工作,同時又兼任母親的一切家務,我與父親相依為命。我常常幻想母親的樣子,也多次問過父親,他說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。父親不想多講母親的事,家裡沒有母親的任何相片,父親自己也不喜歡照相,有一次我對父親說:“母親生前如果留下一張相片也好,讓我看看自己的媽媽像什麼樣子。”父親輕描淡寫地說:“原來有幾張,為了不要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陰影,全燒掉了。”
“阿芳!我這一輩子有你這麼一個孝順的女兒已心滿意足。” 父親常說這麼一句話,尤其是當我有較好的表現:幫助做家務;寒假暑假找一份臨時工;或在學校考一個較好的成績的時候。
我在小城出生、長大。我雖然常感到沒有母親是一大憾事,可父親是一個標準的好父親,相貌不差,菸酒不沾,為人正派,從不向人伸手借錢,父親常說:“我只是一個打工仔,不能寅吃卯糧。你還小,我們在小城沒有親戚,一切生活開支能省則省,你要努力讀書,連你上大學的學費我都存下來了,父親老了就靠你來照顧。”
為了父親,我從小就省吃儉用,從不做父親不開心的事。除對父親孝順之外,還有一點是同情。父親沒有太多的嗜好,工作之外就是下中國象棋,原先是在蓮峰廟的廣場下,後來到孫中山市政(又稱鴨涌河)公園,也常在三角花園出現,我摸透了父親會在什麼地方下棋,放學後如有事找父親,一般都不會找錯。父親每次見到我時,會盡快結束棋局,陪我回家,他下棋只是消遣,不太注意輸贏。

孫中山市政公園 許斌攝
我大學畢業後回到小城,在一次清理家裡的舊物,見到一個塵封的盒子,裡面有幾張女性的相片並穿著不同的民族服飾,也不是同一個人。有黑白相,也有彩色相,不同年代,其中幾張是與父親合照的。父親年青時可真是一表人才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父親與女性合影,是親戚?還是朋友?哪一位是我媽咪?我為自己發現一個大秘密而雀躍,這是不是“一個男人與幾個女人的故事”?還是父親的戀愛史?這塵封的盒子裡面一定有父親一段塵封的羅曼史。

孫中山市政公園 (又稱 鴨涌河公園景) 許斌攝
我曾猜想過父親一定有不想人知的秘密,是一段浪漫的戀愛史?還是一段回味無窮的往事?我想這個謎底今晚可以揭曉,心奮異常。我在家裡煮了幾樣父親喜歡的菜餚,然後撥打父親的手機,他在孫中山市政公園下棋,我要父親回家吃飯,我太想知道今天的發現,如果其中一位女性是媽媽,我可以用掃描製作幾張母親的遺照。
“爸爸!我是不是長大了?”晚餐後我從臥室出來,雙手在背後,手上拿著今天發現的幾張女性照片。
“今天怎樣了,神神秘秘的,是不是要帶男朋友回家讓我看看。”父親說話時眼睛沒離開電視螢光幕。
我在父親的眼前晃了晃一張女子的黑白相,父親臉色一下子變得非常意外,雙目看了我幾秒鐘。用遙控器把電視機關了,然後悠悠地說:“在哪裡翻出這些老古董。”
一張近半個世紀的黑白相片,一個楚楚動人的美人,穿著是東南亞妝扮,而相片底部有中文:『留真』相館及看不懂的外國字,父親告訴我是緬甸文字。
這是父親的第一個女朋友,叫周冰冰,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,在緬甸仰光市照的,我早知道父親是華僑,年青時曾經營過小飲食店,對父親在緬甸的生活就不太知道。
父親出生在仰光市(原譯Rangoon,現譯Yangon),參加當地的青年社團活動,認識了周冰冰。在父親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,到仰光市著名的瑞德貢大金塔等佛教名勝膜拜、到市郊的茵雅湖(華僑稱燕子湖) 等旅遊是必不可少的,與周冰冰到過緬甸勃固市(Bago),該市有世界上最大的瑞達良大睡佛等、到過緬甸南部的毛淡棉市(Moulmein),那裡有一座著名的海心塔,女性不准進入、還到過佛教名山寨梯優(Kyaiktiyo),是山頂的一塊貼滿金箔的大巨石,石上建有寶塔,塔內珍藏數根佛髮等等。從父親講述中可以看出是父親生活中最愉快的日子。
當時仰光常常發生可怕的霍亂病,尤其是在芒果盛產的季節,是霍亂病傳染的高峰期。為防止傳染病漫延,當局設立臨時防預點:在仰光街頭由一名警察和一名護士為單位,查過路人,沒注射過的路人馬上打預防針,開一張注射過的注射過霍亂預防証明。如果拿不出注射過霍亂預防的証明,就強行給你再注射。這種注射防預針有數百個點。當時緬甸仰光市的所有電影院在播放電影前的宣傳片是:用幻燈片放出一隻巨大的蒼蠅,要大家注意霍亂病。由於衛生知識與醫療條件沒現在普及、完善,周冰冰不幸染上霍亂病,也因治療無效而去世,父親傷心了好幾年。之後緬甸社會動盪,華僑紛紛離開居住國到其他國家、地區謀生,父親移民到小城,父親在異國的初戀被霍亂病菌吞噬。
父親照當地政府規定,離境時只充許帶十美元、一只小金介子及一些日用品,父親就是這樣到小城定居。當時小城的就業低,父親到小城的第二天就上班,在一間望遠鏡工廠工作,每日七元,一做就是十多年。當父親三十八歲,內地改革開放,在朋友的介紹下,父親到廣州相親,是一個家在廣州下鄉到英德茶場的女知識青年,她叫岑曉嵐。岑曉嵐的父母希望女兒嫁到小城,因茶場的工作條件及收入都不理想,回廣州到工廠工作更是遙遙無期,而到港澳是一個改變一生的捷徑。這次相親,父親在廣州的時間不長,只有兩天,吃了幾餐飯之外,與岑曉嵐一家到過越秀公園、流花公園、烈士陵園、海珠廣場等公園、景點遊覽,相片就是在海珠廣場以廣州賓館為背景前照的,當時是廣州最高的建築物。
從相片上看岑曉嵐沒有周冰冰動人,父親說當時在緬甸的黑白相是到相館照的,相底有修相這麼一道工序,相片看起來是美觀一些。父親也說周冰冰是比岑曉嵐美一些,當時的父親也年輕,而與岑曉嵐見面時己近不惑之年。父親與岑曉嵐沒有結果,因為岑曉嵐在茶場已有男友,是同班同學。岑曉嵐說:“也不知道父親有沒有老婆,孩子,如果這麼大年齡還沒結婚,一定沒有本事,所以才到內地找老婆。”這是介紹人後來告訴父親的,父親將這話毫無保留地說出來。父親說到這裡時非常瀟洒,對岑曉嵐的話一笑置之。
接下來父親與介紹人到了一個華僑農場,此農場原來有上千緬甸歸僑,也開始陸陸續續申請到港澳定居,父親到了農場之後,連看了幾位緬甸歸僑女子都沒結果,父親在農場的第三天跟一位越南難僑女子倪玉秀訂婚了,並為倪玉秀戴上訂婚金戒。這是父親在小城就準備的。父親在訂婚的儀式上請女方的親戚朋友喝酒吃飯。父親與倪玉秀可以說:同是天涯淪落人,一個要找配偶,一個想離開艱苦的農場,從兩個東南半島國家回到祖居國的華僑,就這樣談妥了婚姻大事。父親與倪玉秀照了幾張相,其中一張在香蕉樹下照的彩色相,看得出倪玉秀臉上的甜美笑容。從相貌上看,倪玉秀比岑曉嵐強,父親對我的看法點頭認同。
一個月後在父親準備到農場看望未婚妻倪玉秀時,介紹人從農場回來說:聽說倪玉秀與一伙越南難僑跑到廣西北海去了。北海是當時從越南逃出來的難民船靠岸購買食物、淡水等補給品的地點之一,倪玉秀等人花錢買通了靠岸購買食物的船主,之後混上難民船,跟著投奔怒海的難民船去了香港,這是介紹人聽來的消息。當時電話極少,只能通信。戴著與父親訂婚戒子的倪玉秀如黃鶴般一去不復返。
事隔多年,當父親說到倪玉秀時多少有點傷感,倪玉秀等乘坐的木船有沒有沉沒?是不是到了香港?後來有沒有到了美國?加拿大?還是歐洲?還是在香港難民營呆了十多年又被送回越南?這一切對父親來說永遠是一個謎。
父親對倪玉秀談不上有刻骨銘心的愛,大約是認識的時間不長,父親說人在陸地上都很脆弱,在茫茫大海上的難民船,風險太高,不要說海浪可怕,就是生病延誤,都會付出極大的代價。這是父親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的尋偶史,留下的是一片惆悵。
當父親說完了認識倪玉秀的經過後,我已經沒有當初想知道秘密的心情了,覺得自己揭開父親塵封的傷痕累累的回憶。我站起來,給父親倒了一杯水,想就此罷休,不再問父親其他女子的相片了。前面的三個女子雖然只留下幾張相片,在父親的生活中的烙痕卻是永恆的。
後面的故事會不會是父親感情生活的另一個傷口?我似乎看到了父親的心在流血,我後悔自己的幼稚,我的好奇心將父親已結疤的傷口再次揭開,我多麼希望眼前發生的一切只是我的一個夢。
客廳一下子靜下來,只有掛鐘發出“的達的達”的聲音。我和父親默不作聲,父親看到我一雙帶歉意的眼光,苦笑地對我繼續說出我想知道的往事。
“這世界上最難求的是“愛情”,愛情可遇不可求。結婚了並不一定代表就有“愛情”,這世界上懂得“愛情”者不多,擁有的更少。”
一段驚人的高論由父親的口中說出,我呆了。以父親的水準,很難說出如此深度的話,這是父親對自己生活的總結!這裡有多少失望、多少無奈,相信很難用數字算出。
又沉默了好一會,父親接著說他後來回到鄉下,在遠房親戚的介紹下,與一位同鄉女子結婚了。就是我母親方小梅,父親指一指其中的一張彩色合照,我的眼淚奪眶而出,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母親相片,我一邊擦眼淚一邊望著父親,他很平靜,慢慢地述說,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。
父親與母親在鄉下正式註冊結婚,因為年齡大加上父親花錢找關係走後門,母親很快到了小城與父親團聚。我記得父親說過多次:在我一歲時母親去世。我常常懷疑母親或許不是真的去世,現在看到母親的相片,再聽父親的戀愛、尋偶史,父親是一個飽受感情創傷的老男人,在感情世界到處處受挫敗。
我已經沒有勇氣去懷疑或證實,母親是不是真的去世,母親的軼事可以不知,不能讓父親的內心繼續流血。
父親並沒有將秘密保留,平靜地對我說:“你已經長大,都應該知道這一切。”父親接著說出的話更是讓我吃驚,原來母親真的沒有去世,而是在我一歲時離家出走,父親以為母親失蹤 ,以為是老實的鄉下女子被人拐騙,父親趕到警局報案。一星期後,找到母親,父親平靜地轉述母親當時說的話:“我感謝你把我帶到小城,我也為你生了一個女兒。我年青,不想跟你生活一輩子。”
父親說到這裡,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後來我父母回鄉下正式離婚了。鄉下,對父親來說,是有過一段溫馨、美好的日子,暫短的,他在那裡結婚;鄉下也是父親離婚的傷心之地,他在那裡離婚了,還留下了對婚姻生活永恆的失望,父親說離婚之後沒有再回過鄉下。
我望著可憐的父親,淚水一串串流下,父親看著我哭,什麼都不說。母親的離去重傷父親的自尊心,如果說情到深處情轉薄,此話用到父親身上一點也不為過,被愛情作弄的父親沒有再結婚,父親也沒有因此借酒澆愁,而是把精力全用在培養我成長。空閒時間就下中國象棋,棋藝不高,因下棋結識一班棋友,有空就下棋,樂此不疲。
“你當時可以再結婚,不是說男人四十一支花嗎?”我說邊抹眼淚邊說。
“單身男子都找不到白頭皆老的伴侶,帶著一個女兒要再婚就更難了。現實生活中不會有好的繼母,電視連續劇中可能會有,那是作家編出來騙人的。”父親指指電視機輕描淡寫的說,父親的語氣也稍微減輕了我內心的過錯感,今天的幾張相片把父親拖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生活,我也如時光倒流般一下子看到當時的人物,生活,對父親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層。
“小城不大,這麼多年來你有見到媽媽?”我這麼大第一次對著父親叫媽媽。
父親點點頭。“有一次進大陸,在拱北關排隊時看到她排在我前面,隔著好幾個人,她沒看到我,她跟一個男子在一起,很親密。我怕她回頭看到,我退後去洗手間,慢慢洗手,拖延時間,然後重新排隊。我們雖然離婚了,撞到總是會尷尬,我是老頭,無所謂,這樣對你媽不好也會讓她身邊的男子產生誤會。一日夫妻百日恩,我們也做了兩年的夫婦,她能幸福生活我也開心,我常祝福她。”
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父親嗎?小說中以德報怨的男主角也不過如此。
夜深了,我躺在床上,久久不能入睡,我失眠了。
父親呢?會不會也失眠?
從父親的房間傳出如雷般的鼾聲,我鬆了一口氣。這些往事對我來說是新鮮事,對父親說來己是陳年舊事,漫長的歲月早已療癒了他的傷口,雖然當時傷得很深。
我母親還活著,就在小城。如果要找她應該不難。我有必要見她嗎?見到母親我要對她說什麼?第一句話是不是問:“為什麼…?”

澳門三角花園 許斌攝
转载请注明:《父親的愛情故事(許均銓)》 复制链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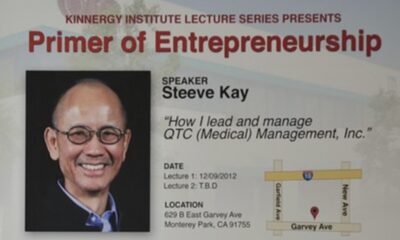






-2-400x24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RSS